閒話張愛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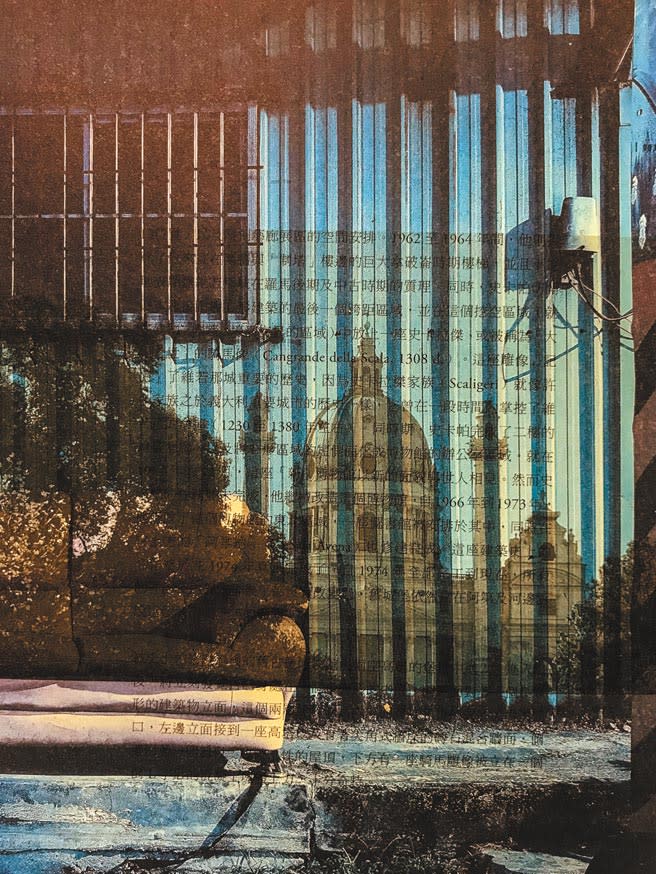

九五年張愛玲離世,數日後為人發現,老婦孤獨,死無人收。骨灰臨空一撒,自此人間再會,遙遙無期。去年逢張百歲,雜誌社找來寫手,連刊三期,用文字辦了三個月的法會,供起祖師奶奶。為文字而生的人,以文字遙祭添香,得其所哉。
張有篇〈重訪邊城〉,看文題以為她去了沈從文的湘西,一讀才知,「邊城」是台北。
華人世界的張愛玲熱,無城能及台北。有朋友去了一趟台北座談,回來若不經意提及,掩不住「進京」的喜悅。文化事業常年度小月,高鐵來回吃掉演講費的一半,撙節經費已是浮上檯面的守則,坐捷運就能到的,何須召請坐高鐵的。這個問會計部門,最是明白。
張看台灣是孤島,上海、香港何嘗不是。她寫上海公寓,一逕溼答答,浴室、水龍頭、熱水管,梅雨時節的門前積水,牆根汪著水漬,斑斑點點的水痕,黃包車渡過白茫茫的護城河,碧藍的瀟瀟的夜,彷彿寫字檯前撐把傘。終究是自家巢穴,有自己的一份,小天地也能窺見萬象,賞不盡的新鮮適愜。
讀張愛玲,猜想她的窗夠大,然而房間暗,地板冰涼,進來的月色才夠好看。這個我實驗過,自家打一井天窗,七尺見方,果然月上中宵,地上一層霜。
甚麼是邊城?近年幫幾個長輩代班,到南投嘉義上課,開車的出版社業務說,台北下來轉車進去,走的是國道高鐵,來回一天沒了。去到現場,底下的眼色說:這個城裡來的。待我說起當年上班如何的灰頭土臉,上下才呵呵通了一氣。
張有篇散文寫洛杉磯,空曠乾燥,廣漠荒涼,以為她去到了月球。時間近乎停頓的緩慢,目光還是匆促的,掃過懶再回眸。雖然也寫了公路汽車,房子店鋪。公車站牌下的一行字,一個姓魏愛著一個姓戴的,年輕孩兒興之所至的塗鴉,費了她大半篇幅,簡直考古一塊史前墓碑。
張是一票作家的起家厝。她給的,早比她寫的多了更多。張給林以亮的信,當年文壇炙手的,她不暇一顧。同事阿妮塔頗為這開心:原來我倆所見略同呀。有種被理解了的撫慰。
我提醒阿妮塔:張愛玲可能生病了,吃了惹她煩躁的藥,閱讀的胃口才弄成這樣。
張和木心,都有教主派頭:一定質量的作品,前仆後繼的徒子徒孫。縱有庸常之論,教主說了算,如仙人打錯的鼓點,於凡人耳中仍是灌頂的仙樂。偶犯貧嘴,他人學舌,就是刻薄,欠掌嘴。住得離眾人愈遠愈好。如果居板橋永和,三天兩頭被捕獲,要此地的人拿她是佛,怕是難了。
且被拱成教主,底下必然有護法,有盜竊者。不善學的,學她的腔,一句月光,一句滄桑。八十年前的聲腔,此時此地哪裡堪用。
張來台北走訪的廟,也許在萬華,大稻埕。有尊神農引她莫大興味。想來有她原先見慣了的神佛,遂於這樣一尊,生出種種比附猜想。那股新鮮,似我們在看婆羅洲的祖靈。張也愛看人公車上打架。若今日她也上網,住台中,這類的影音夠她瞧了。
見了好看的花樣,就想裁來做件衣裳,合了腰身,就算自己的。她離開共產黨治下,恐是憂日後沒有自身可穿的衣裳,等於沒穿。
〈重訪邊城〉也寫及香港。不住地跟夜色計較,街道這樣黑,這麼暗,香港脫卻戰爭多年,偏安的小太平,水電無缺,早非當年躲槍林彈雨的圍城,張卻一路詫異:黑,暗。上海〈公寓生活〉寫電梯棕色的,紅棕色的,黑色的各種黑暗,也還是迷心撩亂。現下除了捨不得早歸,也是當年浮沉於最富色彩的時光褪了色,從彼處回望的此刻,怎麼都不明亮。
離港前不知何處飄出的一縷穢臭的滫氣,張執迷地嗅著。像追聞深巷樓台咿呀的胡琴,昔時來過而不再回返的,使人心酸眼亮的流光。
張的文字搭設的後台那邊,多的是東西。讀者像去到一處繁盛的園林,走逛一回,花徑怎麼鋪設,池泉如何布置,疏影橫斜怎麼呼應月光,回來一邊覷看自家花盆,一邊揣想那園子,就開通了。下回再過去流連,又生出新的看法。如此往復不絕。用張自己的話,「從兩行之間,讀出了第三行」,是「一生二,二生三生了萬物」的道理。
林以亮說張是作家中的作家。好作家都有這東西,張特多,處處盎然,無怪乎掘藏者夥,繼之者眾。她的〈炎櫻語錄〉,有人懷疑若干或是張的自語,推給炎櫻。有才者不愁無米可炊,分一些給別人也沒甚麼。
常人習慣說寫作是「筆耕」,汗滴禾下土,字字顆粒撿拾,貫串成句成章。村上春樹更硬,說是「挖礦脈」,穿透到堅硬岩石的心臟,泉源汩汩冒出,像是挖井,額前箍住一頂探照燈,下去再下去,直至無人能及的深淵。
早年的版本鉛印字年深歲久,漶出了毛邊細絲,成一朵一朵水面排列的字花,浮在昏黃的紙頁上。圍城、家國,百年過去,物事全非,張的文字仍在。張本想撒骨灰於空曠荒漠處,後來水葬。李永平、七等生也是,免去煩人的祭奠。來人想跟上的,就去文字裡推敲琢磨,所謂「精神基因」上的徒子徒孫。
學者們諍論祖師奶奶的「祖」字,示從且,「且」是陽物之徵,「祖」字就是男人渴望自身基因綿延的執念了。
阿妮塔家族有個長輩,晚年在外生了一子,遺言財產悉數給他,圖的是「死後有人拿香」,這一念攪得家族翻騰不休。說起這一廂的情願,傳了三代還有人祭奠,都算福澤綿長了。若問晚輩這墓中屍骸的生前行跡,只怕無人能說得半件。眾子孫立在墓牌前,也不及讀一篇小說的時間。
阿妮塔又聊起市場聽來的八卦:某家媳婦逢節祭拜祖先,只一盞碟子,擺一張千元鈔。春節兩張。拜完的鈔票買彩券,中獎機率一般。
阿妮塔見過那婦人,不像做這種事的。
「這誰講的,這事她怎麼敢講。她若沒講,別人怎麼知道。」
「看也不像是自己說的。」阿妮塔說。
所以,到底講的那個人是誰?
她造了一座小小的富麗的荒園。
美人,公子,前仆後繼的徒子徒孫抬她的鑾轎
咿喔咿喔學步,亭子裡幽幽的管絃。
她死後,有人在牆外:「是個寂寞的園子呢。」嘴裡這麼說。
又造了一個園子。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