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沉默沉澱成一首長長的無言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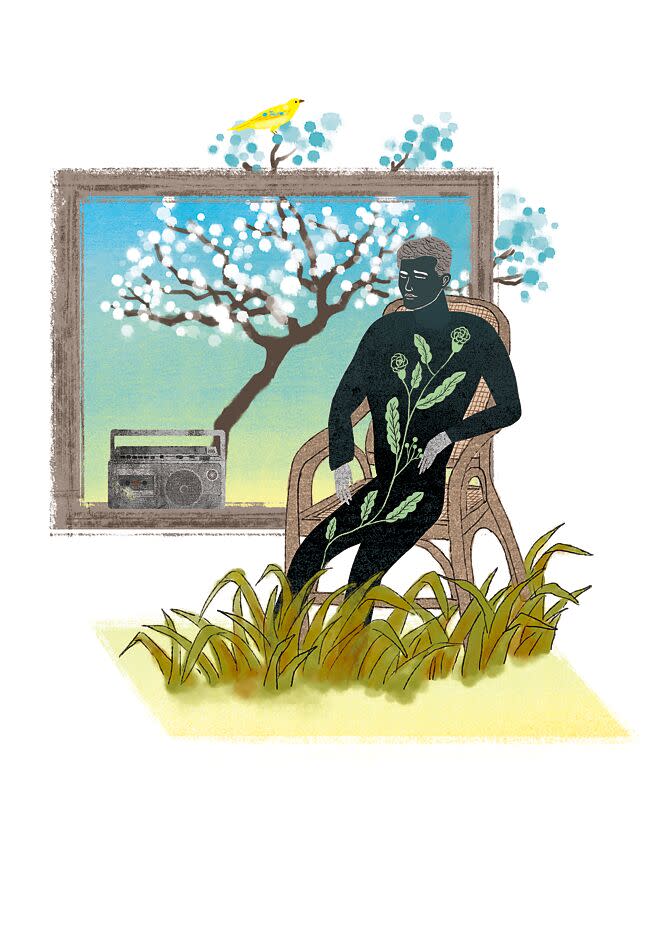
退休後,她返回娘家的次數變多了,主要是為了探望九十高齡、記憶力已然嚴重衰退的老父,其次是可以坐在亭子腳,靜看熟悉且彷彿含有情感的山川草木,好沉浸在童少記憶中回味老家的溫暖。不過這一次,她的腦子卻塞滿富國屘叔的五十年沉默和被沉默閉鎖在房間裡的身影,因為兩個禮拜前,她手機上的家族群組出現堂弟的留言:「阿叔昨天往生了……」。
家族的微薄房產由伯父繼承,伯父也在祖母去世那年,繼承祖母挑起照顧阿叔的擔子,近年,伯父即使「毋甘(不忍)這個小弟」,但耄耋體衰,想繼續挑擔也已力不從心,只好同意自己和阿叔都被遷移到養護機構定居。一個月前,堂弟告知眾親人,他已遵照社會局的安排,將阿叔安置到某某療養院,稍後阿伯也搬到一家養老院,豈知才過兩個禮拜而已,阿叔就真的永遠沉默,或者說告別沉默了。
那天堂弟在留言中還說,他會辦理阿叔的後事,一切從簡,不必勞動大家,尤其不要勞動長輩,他也暫時沒跟住在安養院的父親(她的阿伯)、二叔(她的父親)和兩位姑母說。堂弟還表示,是否讓這四位長輩知道,就請各人看情況決定。結果,大家一致認為,除了阿伯,阿叔的另外三位兄姊都已數年沒回老厝,而且也都可能忘了老厝住著一位沉默五十年的小弟了,就不必再去撩撥他們的短暫記憶和喚醒他們的傷感。而她,也和其他兄姊弟妹一樣,都依從堂弟的交代,沒去目睹阿叔的遺容。
在她這一輩的叔伯兄弟姊妹中,除了大姊、二姊和大哥三人還有幸能與尚未閉關的阿叔有所交集之外,其他人對阿叔的印象大概就只剩下終日「覕嘴毋講話」的記憶了。這樣,阿叔的離世對她來說應該很容易就淡然處之才對,可是這時她卻感覺相當難過,忽然想起一件往昔的疑惑,使她產生一種來不及彌補的愧疚感,那是三十幾年前,她從鄉下調到市區的大學校任教後,知道學校有一種獨立於各年級的特教班,專門輔導校內的少數幾位具有某種學習障礙的孩童,當她認識特教班的老師且交談幾次後,開始知道有一種叫做自閉症的心理障礙及其部分特徵,她也實地去看過特教班的那個有自閉症的小孩確實很沉靜又不愛和人說話,這情形讓她立刻想到自己的屘叔敢情也是患了自閉症?不是吧?阿叔是大人,是二十幾歲才忽然「半暝食西瓜反症」變得緘默不語的。因此,她便沒繼續探究,也沒想到大人也可能由於某種因素而「亞斯柏格」起來。但不管阿叔是不是自閉症,她想,當年她要是能跟阿嬤、阿伯等平時和阿叔同一屋簷的親人談說自閉症候群,叫自己,也勸親人們能和阿叔多些相處並說話,而不是放任阿叔閉關獨處,把沉默寡言煉化做沉默不言,也許會有機會讓阿叔走出沉默!此刻浮現這段記憶,使她感到一點自責,或許也是這個緣故,沉默阿叔的影子才會在這個時候盤據著腦海。
既然已經往生的阿叔這時來到她的腦海,她決定把阿叔的沉默拉出來,將她對阿叔的記憶化做文字。於是她回到屋裡的書桌前,提起筆準備寫下阿叔的沉默。要怎麼寫呢?她想著,同時眺望窗外的山巒,一陣子後突然覺得家鄉的群山懂得叔叔,也聽得懂她要說的沉默,不是短暫的靜默,不是有話鯁在喉嚨嗑不出來,也不是一時不想講話,更非嘴脣偷懶,尤其不同於住在村後那個綽號「啞口輝吔」的啞巴。然後她把山當做聽眾、當做讀者那般開始用筆訴說:
阿叔像一支孤獨的山,不講話已經五十年。去年農曆過年前,我和大姊、二姊回娘家,相約回去老家祖厝看阿叔,我們知道在阿叔的房間外叫門是得不到回音的,便逕自推開沒有內閂的門走進去,阿叔削瘦的身子坐在床沿,看到我們並無新的表情,「我是阿美,伊是阿貞,啊伊是阿慧」大姊說,我們靠近前,大姊再問:「我阿美啊,你咁會記得?」阿叔舉高右手,好像要摸大姊的頭,我們都震驚一下,微微後仰,也許阿叔只在打招呼,呆滯的眼仁隨著頸椎轉動一下,好像讓虛弱的眼光輪流停在我們的臉上,他的嘴脣動了一下,卻沒放出聲音,只以輕微的點頭代替回答後,就把手放回去,已經至少二十多年沒見面,想不到阿叔還記得我們。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阿叔的沉默竟然這麼濃密、這麼強有力的瞬間就感染了我們,以致這次會面的時間被極度濃縮了。到底阿叔掩藏在沉默裡的,是什麼樣的感情?
我無法確定,將近五十年的累積,阿叔的話是否已在他的體內擠得水洩不通,連一個詞彙、一個語音都找不到隙縫鑽出來。要是這樣,那些簡單的招呼語和複雜的情緒句在枯瘦狹窄的空間裡是怎樣安然相處呢?而那些性格相異的話,快樂與悲傷、溫熱與凄冷……,會不會在阿叔的心中爭鬥吵架,讓他苦不堪言而更加沉默?也許在阿叔的嘴脣完全關閉後,話就跟著停止生產了。
這次見面,她認為阿叔的沉默會繼續堅持,但她覺得阿叔其實也想把話吐出來,只是他的話不知為何羞怯不敢見人,一浮出嘴孔就躲在嘴脣後面。而現在,人已往生,嘴脣沒有了,話語就藏入骨頭,叫火焰也烤它不出,轉而化做粉末躲進骨灰裡,縱使一切都消失,他的「沉默」還會在,阿叔的話總會找地方躲藏!想到說話,一幕小時候與阿叔對話的影音馬上浮現,她寫著:
可是,我記得我讀國校時,阿叔還會跟我們講話,那時,阿叔常會打開房間的門,看到我或堂妹,就會喊「阿慧」或「阿芬」,接著伸出拿著一張十元鈔票的手說:「去捾一罐『一陣風』」,起初我們還以為阿叔「寒著」感冒了,才叫我們幫他買感冒糖漿,後來發現,原來阿叔把「一陣風」當做飲料,喜歡它的略帶甘甜又有一點芳香的味道。伊的每個侄孫都期待這種好差事,因為我們知道阿叔不愛出門,決不會自己去買,就可以趁機跟他揩油,刁嘴說:「找的錢要予我買糖唅哦?」我們金爍爍的眼睛早就把他那癢在喉嚨的渴望看得一清二楚,等他應答出那串軟弱無力的話:「五角,干單會使哩予你五角。」,才歡忻的接過那張印著一個人頭像的紅紙鈔,轉身走向村子唯一的篏仔店,步伐也像踏著一陣風。嘻嘻!五角,很多啊!那年代,我們跟掌管家務的阿嬤討零錢時,每次也只敢要一、兩角呢!所以我們有時在門口玩耍時,往往也會邊玩邊看阿叔的房門是否打開一個縫。
阿叔的房間有一扇窗,如果把掩蓋著窗的柴板撐開,他的房間也會和阿嬤的房間那樣掛出一幅鄉村的農家圖,清晨,阿叔可以看到住在後鄰那戶親戚在擣洗衣衫、晾曬衣衫,穿著炫麗的火雞在竹籬內箐翻沙土、啄食蟲子;黃昏,阿叔可以看到埕斗上有男孩在玩閹咯雞、覕相揣,唸著:「點仔點水缸,點著啥麼人仔爛尻川……」,或者欣賞女孩在玩疊沙包,一邊拍掌一邊唱唸:「一放雞,二放鴨,三分開,四相塔……」。衣衫火雞囝仔與大人反向看過來,也會看到一幅光線柔弱的靜物圖框在阿叔的門窗裡。可是阿叔不要寫生,也不想素描,即使做出一幅畫也不讓大人、囝仔和衣衫、火雞觀賞,他不管什麼時候都把窗板放下來,即使他喜歡的微風,還是討厭的暴風都被關在窗外,只有裝在小玻璃罐裡的「一陣風」可以敲開一小縫阿叔的門窗,讓「一陣風」和剩餘的銀角仔(零錢)交付到阿叔的手中,接下來我只能想像阿叔怎樣微微張開嘴脣,讓液化的風一陣一陣緩緩的流入嘴巴、流過喉嚨,澆沃他的長期找不到出口的話語。
她搜遍記憶庫,才找到一、兩句和阿叔的簡短對話與相關影像,都是發生在阿叔想買「一陣風」時,因此寫到這裡,她突然自覺幼稚地在心裡問道:是不是一陣又一陣的「一陣風」把排好順序的話語吹散了、沖亂了,使阿叔的話語失去了方向,更加走不出身體裡的迷宮,而更加滋養了他的沉默?自問無答後,立刻想到比她年紀大的親人其實也有收藏屘叔在沉默之前的更多出聲記錄或生活影音,就繼續回憶繼續寫:
阿叔曾安置一綑影片在大哥的記憶裡,以前大哥常放映給我們看:(台語)「阿叔少年的時偌巧偌緣投咧!彼當陣,我讀國校仔,阿叔猶佇做兵,伊見擺放假返來,攏會去園裡鬥做空課,佫會若做穡若唱山歌,隔轉工收假,欲走的時,參阿嬤相辭了後,上愛對我笑一下講:『我是軍,你是民』,就開始若蹔跤步若唱『我現在要出征』彼條軍歌,佫會改歌詞唱講:『你阿民要同行,唉唷阿民要同行,你同行絕不成。因為我是軍,你是民』,對我搖兩下仔手表示再見,才斡出巷仔口。」我們聽了也哈哈大笑,因為大哥的名字有一個字「民」!看來大哥保存的這綑軟片至今沒有磨損。阿叔活潑的形象就這樣copy在我的腦葉,原來阿叔也曾經這麼風趣!那麼,到底是什麼把阿叔的開朗禁閉了呢?
阿叔放在阿嬤頭殼裡的一段影片有透露原因嗎?
「阮國仔哪有安怎!阿就有一遍去店仔頭看人行棋,國仔人巧看較有,加講二句,彼个行輸的煞見笑轉受氣,罵伊:你偌敖,遐敖哪會食甲欲三十矣猶是羅漢跤仔一个,無某無猴。阮國仔面皮薄,互罵一下感覺見笑,自安呢攏毋出門,嘛較無愛講話。」
有人問起是安怎阿叔不講話,阿嬤總是這個答案,說給問她的人聽,也說給自己聽,說給自己聽時,有時還會補一句有聲無力的埋怨:「遐夭壽!加阮國仔害甲安呢!」
這個短短沒幾句的版本似乎無法解開阿叔超重的沉默,卻負載著阿嬤長年的苦痛,我們知道阿嬤的眼睛和耳朵一定收容了最多阿叔演示的影音,為了不增加她被回憶的痛苦所折磨,我們不問也不在她面前談論阿叔的點滴,並接受阿嬤唯一提供的這一條線索。(待續)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