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威全專欄/高嘉瑜左打柯文哲,右打徐巧芯 都計概念卻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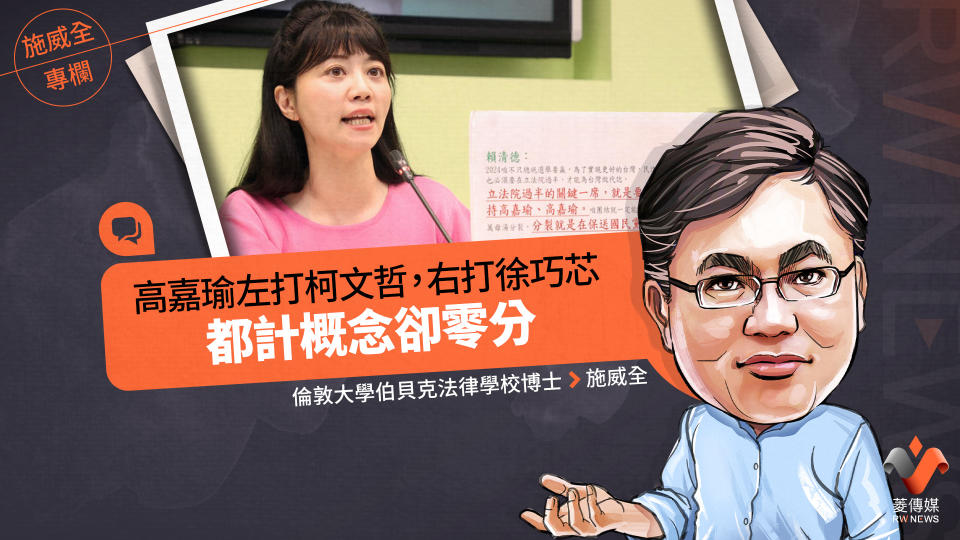
施威全/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高嘉瑜追打京華城案,左打柯文哲,右打徐巧芯,一白一藍、政治對手被描繪為圖利/得利的同一陣線,高嘉瑜對於京華城容積增加的過程有明顯錯誤的描述。
高嘉瑜說「京華城容積率解套有兩大關鍵時間點,一是從392%到560%,靠當時監委劉德勳的糾正文…但原監委已調查完成不同意560%容積率,被劉德勳接手翻盤逆轉成560%。」
監委劉德勳提案糾正前,監察院的確早有定論,在2013年11月12日提出調查報告發文台北市府,認為台北市政府要求案主以容積率392%進行修正不合理、「實有未洽」。劉德勳擔任監委始於2014年8月1日,這份認為台北市政府不對的調查報告與他無關,內容也與高嘉瑜宣稱的「不同意560%容積率」完全相反。
劉德勳任監委就此案又提糾正,不是翻案,是因為業者又向監察院陳訴,而原來的監委已卸任,所以分給他接手。劉德勳不是翻案,也因為他提案糾正的內容與先前監院的調查報告一致。
高嘉瑜的說法兩大漏洞,一、把最早的監委調查結論,她顛倒黑白;二、把責任亂栽給劉德勳。
京華城容積率到底是392%還是560%,最早的監察院調查報告立意清楚,392%指的是整個街廓土地的粗容積,業主捐了地,扣除30%捐地範圍後,剩下區塊之容積率應為560%。台北市政府在2018年發布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也引述了此看法,更重要的是,在這份「細部計畫案」裡對於為何台北市政府認為是560%而非392%,提到了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決議:
「本計畫案之修訂係市府依監察院糾正文、審核意見及內政部函文意旨,釐正80年2月13日都市計畫書有關容積率之規定,於本次修訂計畫案明確載記容積率為560%,本會無權置喙,予以尊重。」
都市計畫委員會尊重的對象有三:監察院、內政部,以及送出計畫案的市府都計權責機關,最重要的還是做出決定的市府都計機關,不是一人一院逼使都市計畫委員會「無權置喙,予以尊重」。
到底都市計畫委員會是依法沒有權力認定容積率,還是不想擔責任,從該會的決議看來,模擬兩可。作為有外部委員參與的會議,在臺灣引進「開發許可制」處理既有的「土地分區」議題後,都委會在實務上其實把手伸的很深,都計學者、建築學者職責在審議都市計畫內容與開發案的合理性,辯論好或不好,但在行政法的角度、人民與國家的權力義務關係上,卻常撈過界。針對京華城案,常撈過界的都委會卻又龜縮,讓監察院、內政部與市府內部機關扛責任。
臺灣的土地使用分區源自美國,但這套制度在美國也是都市計畫紛亂的根源,例如downzoning這個字,很長一段時間在美國東岸指的是把低密度開發改編為高密度開發,同樣的字對美國西岸的法律人、規劃師而言,則是完全相反的例子。1950年代始,面對僵硬,而且常引發司法審查的土地使用分區,美國逐漸引進英國式的開發許可制,企圖在僵硬中找到靈活、配合都市發展趨勢的混血方式,這個調整,30多年後臺灣也逐步跟隨,現行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就擔負了部份開發許可制的功能,公家機關不敢自己扛,找外部人士來分擔審議、核可的責任。
開發許可置在臺灣的應用,最早掀起軒然大波的就是南隆案,南隆工廠由工業用地變更為商業用地,監察院還調查陳水扁任市長時的都發局長張景森;此次京華城案,案情類似,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回饋與容積。這類案子容易扯上政治爭議,在於開發許可制的本質就是給予公部門相當的裁量權,企圖在硬性的規則下有彈性作法,這在臺灣產生兩個後遺症:一、公務員怕圖利開發者,有專業能力的文官扛不住責任,只好把責任往上推,推到政務官、推到市長。二、不敢行使裁量權,便一直增設行政規定,以便規範如何裁量,變得各式規定鉅細靡遺,違反了開發許可制的精神。
英國的開發許可制,建立在把土地發展權收歸國有的精神上,這違反了英國普通法,因為普通法源於保護貴族的私有財產,英國的開發許可制便是國會以立法權對抗普通法的產物;美國的土地使用分區,在行使上也常出現兩種法律意識形態的對抗,行政權對發展的限制對抗了憲法對殖民者財產權的保障。不管英國的開發許可制或美國的土地使用分區,法律人在設計時都必須考量會不會受到司法審查機制的挑戰,而法庭也常藉著判決形塑了城鄉規劃法規的面貌與都市的發展。
英美事務移植到臺灣後很不一樣,制度的主要推動者不是法律人,因此在衡量個案時,有能力考量合理性、好或不好,但主要關注不是土地所有者的基本權益。同時在實務上臺灣少了適當的司法審查機制,合理的法律或行政訴訟機制甚至被堵死或很難走,這點在監察院關於京華案的第一份報告裡也有點出來,京華城案曠日廢時就是南橘北枳的具體例子。
不是責怪在公部門的城鄉工作專業者,因為現行的制度,他們一方面要以上帝視角關照所謂的全體市民的公益,同時又要站在開發者的權益立場為其開創利益,兩個衝突的角色都要公務員扛,不可能。但當高嘉瑜等人將此案政治化時,美國環境法先驅、威斯康辛法律教授Jacob Beuscher的名言可以提醒各方爭論者,在他談論法律與區域發展的關係時,那時還沒有環境法這名詞。他說:
「通常我們把法律當成靜止而非動態,我們的法庭、立法機構、行政單位創造了法規,但法不是因此就完成了,法應是達成政策的工具…我們的迷思是,法律是限制、是煞車,其實很多法律規則是具有效能、彈性調整,引導發展與改變。」
談京華城,不該把容積率加大就當作弊案,是不是弊案,就查柯文哲有沒拿錢,有沒有利益對價關係,查不到,就不是弊案。政治人物如果繼續吵容積率該多大多小,那就乾脆廢除開法許可制,連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從此也都不能動。

菱傳媒原始網址:施威全專欄/高嘉瑜左打柯文哲,右打徐巧芯 都計概念卻零分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