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副刊〉被西方藝術史忽略的篇章
文/韓秀 圖/簡昌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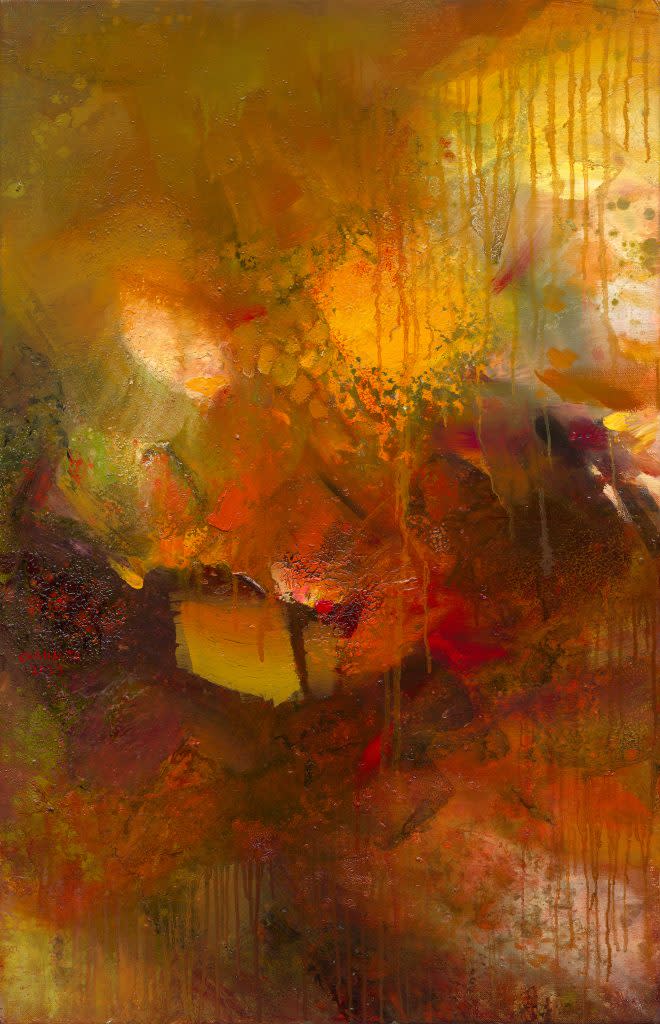
西方藝術史中的佼佼者們的事蹟出現在後世人們眼前的時候,都會或多或少地被留下藝術史寫作者個人好惡的痕跡。除非是板上釘釘、鐵證如山,完全無法迴避的情節,握管人只好將個人背景、立場、觀感稍作收斂,在正文中將自己不感興趣的部分一筆帶過,或是隻字不提,只在藝術家年表中以最簡方式列出。
在被扭曲、被簡化、被忽略的篇章中,藝術家們的情感世界為最。
李奧納多‧達‧文西最為幸運,因為他早早就嚴絲合縫地關緊了情感的大門,將全部的精神力氣用於發現、發明與創造。然而,關緊情感之門前那一瞬,關係到的是佛羅倫斯名媛吉內芙拉‧本琪。一幅肖像的繪製,以及一次在庭園裡的擦身而過,便是兩人之間的全部。實在「無可厚非」,也無從恣意擴展,於是彗星般地留在了藝術史上,成為永恆的美麗。然而,將肖像交給委託人之後,李奧納多的椎心之痛畢竟還是被藝術史家們不經意地忽略了。
米開朗基羅相當幸運,他與貴族遺孀柯隆娜相遇在光天化日之下,相識的媒介乃但丁的詩歌。柯隆娜住在修道院裡,米開朗基羅不但將柯隆娜繪入素描《聖殤》,而且把她的倩影融入西斯汀禮拜堂濕壁畫《最後的審判》中的聖母形象。藝術史家忽略的只是兩人之間相知相惜的程度,換句話說,這份相知相惜並非歷代藝術史家所能真正理解,因之少了穿鑿附會。
比較幸運的是卡拉瓦喬,這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騎士所幫助的全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女子,藝術史家們冷漠地一筆帶過。留下的寥寥數語則是藝術家對於出身科隆納家族的女侯爵遙遠的思慕。毫無疑問,在卡拉瓦喬攸關生死的關鍵時刻女侯爵多次出手相救,將其留作藝術史上的佳話,沒有什麼不好。
塞尚則與情感「無關」,乃其性格使然,雖然他結婚生子,雖然他為妻子畫了大量肖像。藝術史這樣告訴我們。真的?情感被徹底壓抑是塞尚的不幸。他有沒有嘗試過解脫?當然有,只不過藝術史家對於那慘敗的嘗試不屑一顧罷了。這就使得後世的人們看待塞尚能夠感覺到更深一層的理解與親近。
杜勒遵父命成婚,終其一生沒有嘗到愛情的滋味,沒有子嗣,亦完全地沒有萌生任何的夢想,幾乎過的是修士的生活。藝術史上有關他的情感世界完全留白。同塞尚一樣,他們都熱愛母親,母親是他們藝術事業永遠的、堅定的支持者,從無遲疑。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歷代藝術史家都沒有下足功夫研究,更沒有認真書寫。
天之驕子拉斐爾初見美麗的少女安撫狂躁的天鵝,首先想到的是前輩李奧納多的名作《麗達與天鵝》,當他知道這位女子是麵包師的女兒,便以義大利文的發音喚她芙爾納瑞娜。待他們成為戀人,拉斐爾才知道她的名字是瑪格莉特‧路蒂。瑪格莉特在義大利文裡是珍珠的意思。這位珍珠般的女子卻因其「出身的低微」而不能與拉斐爾結婚。拉斐爾要守住這份情感必得想盡一切辦法抵禦紅衣主教貝畢那的煎逼。好在教皇利奧十世愛惜拉斐爾,委婉地阻止了貝畢那的奸謀,使得拉斐爾較為順利地保有了這份情感。拉斐爾只有三十七年壽命,臨終前交代助手們要好好照顧瑪格莉特的生活。但是,連喪禮都不能出現在眾人面前的瑪格莉特知道,她只能帶著拉斐爾的一幅自畫像逃離羅馬,才能躲開貝畢那的迫害。於是,「麗達烘焙」出現在遠離羅馬一個山明水秀的小鎮上。藝術史家們從來不屑於提到瑪格莉特與拉斐爾的情感,也從不研究,拉斐爾那幅著名的題為《年輕男子肖像》的自畫像為什麼在拉斐爾逝後兩百餘年才在世上出現,瑪格莉特‧路蒂以及她所託付之人在這樣漫長的歲月裡是怎樣周全地保護了這幅作品。沒有,歷代藝術史家對「出身低微」的珍珠沒有興趣。
藝術史家們對埃爾‧格雷考的一生摯愛荷瑞尼瑪‧圭佤司不怎麼上心。這位有著摩爾血統、猶太血統的西班牙人,能閱讀希伯來文聖經也能閱讀阿拉伯文古蘭經的奇女子,因其「血統的不純正」,因其宗教觀的「不尋常」而成為西班牙宗教異端裁判所監視的對象。埃爾‧格雷考本人來自希臘,在宗教異端裁判所的鷹犬們看來也是屬於「異教徒」之列。無法結婚的苦命鴛鴦有了兒子,母親卻被瘟疫奪走性命。身為父親的藝術家為了兒子的安全而以舅舅的身分養育了自己的骨肉。因之,荷瑞尼瑪的美好悄無聲息地走進了藝術家的作品,成為聖母的形象。在《奧爾卡斯伯爵的葬禮》中,一家三口天上人間同時出現在畫面上,謳歌的便是藝術家殷切期盼的團圓。其他都是次要的,團圓才是主旋律。而父子之間的血緣關係則在托雷多聖約瑟夫禮拜堂的祭壇畫中得到印證。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藝術史家們輕輕帶過,並沒有特別珍惜。襟懷寬廣的知識女性荷瑞尼瑪更沒有佔據藝術史家們的研究時間。
林布蘭曾經有過堪稱幸福的婚姻,但是兒子泰特斯一歲之時,母親莎斯琪亞就去世了。比林布蘭年輕二十歲的韓德麗琪走進了林布蘭的生活,無微不至地照顧了林布蘭父子,帶給林布蘭平靜與祥和。他們無法結婚的原因是莎斯琪亞的遺囑。沒有一紙婚書的兩個人不但生活在一起,而且生了一個美麗的女兒。在當時的荷蘭社會,韓德麗琪受到輕蔑與教會的迫害。然而這都沒有改變韓德麗琪對林布蘭的感情。只活了三十七歲的韓德麗琪留下健康的女兒與林布蘭相依為命。莎斯琪亞出身富裕家庭,死後葬在富人的墓園。林布蘭與韓德麗琪卻早已屍骨無存,因之,今日的遊客們希望看到林布蘭家人的墓地,只有莎斯琪亞安息之處可以造訪。在西方藝術史上,美麗的莎斯琪亞是女神,美麗的韓德麗琪是女傭人。然則。我們卻在林布蘭的偉大創作《浴女》中看到產後明麗的韓德麗琪,在《花神》中看到端莊雅靜的韓德麗琪,更在一六五九年創作的《韓德麗琪肖像》中看到雖然病苦,卻依然堅定沉著的韓德麗琪。在林布蘭心目中,韓德麗琪是可以共患難的家人,是無上的心靈慰藉,更是情感之所繫。歷代藝術史家虧欠韓德麗琪太多。
J.M.W.透納的情感世界在藝術史上幾乎全無蹤影。透納生前以母系家族姓氏馬洛德與民宿主人布斯夫婦交往。短短三年中,布斯先生不但失去獨子而且駕鶴西去。布斯太太索菲亞失去了前後兩位丈夫、兩個兒子。透納不但照顧了這位孀居的婦人而且教導了索菲亞在第一次婚姻中存活下來的兒子。終於在數年後,兩人之間有了親密的關係。這樣的關係維持了十六年之久,透納生命的最後五年完全仰仗索菲亞的精心照顧。透納辭世之後十年,索菲亞的兒子才得到母親的同意售出透納留給他們的部分畫作。透納辭世之後,索菲亞獨自生活了二十七年,帶給她幸福與快樂的「馬洛德先生」從未離開過她,在透納作品的環繞中,在透納旅行途中寄來的信函、詩歌、素描中,在溫暖而充滿詩意的回憶中,索菲亞度過了漫長、美好而平靜的歲月。這樣的一份情感,這樣的一位女子難道不讓藝術史家們感覺好奇嗎?沒有,他們對於「無知無識」的索菲亞毫無懸念,毫無興趣。索菲亞的名字只在一些著述的附錄年表中出現,簡短而不知所云。他們甚至沒有想過,透納晚年那些「為自己的眼睛」繪製的畫作,那些在二十世紀才被發現的「跟著感覺走的現代藝術」,最早的觀者、最早的評論者正是名不見經傳的索菲亞。
要知道,偉大的藝術家們不是藝術史上的一個個符號,他們那許多偉大的作品不只是在博物館裡被人們爭相拍照的展品,而是聯繫著他們的美學觀念,聯繫著他們對世界甚至對宇宙的認知,也聯繫著他們的情感世界的心血結晶。藝術史的撰稿人、藝術家傳記的撰稿人應當能夠從浩瀚的史料中探尋到並洞悉這一切,珍惜之,並能夠以尊重與理解之心為這些有血有肉的人們勾勒出他們生活的確鑿軌跡、他們的奮鬥與建樹、他們的脾氣與性格,以及他們真實的情感世界,並且不帶任何偏見地書寫出來。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