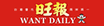兩岸史話-溥儀夢碎滿洲國
旺報【文╱李念慈】 老一輩日本軍人的「中國通」,沒有中國,他們的功名,便也無所寄託,他們謀中國之心,不必有愛於中國。 板垣征四郎有「滿洲國」專家之稱。他由參謀副長,升任關東軍參謀長,以「滿洲建國」的「產婆」,掌握「滿洲國」的內面指導權,日本人呼為「專家」參謀長,負有日本朝野的重大期待,視「大參謀長」小磯國昭,有過之無不及。 塘沽協定簽訂前,板垣在天津的工作,一無交代的不了了之,板垣自身亦極感牢騷,返回奉天,便辭去特務機關長,出國遊歷。翌年「滿洲帝國」成立時,故由歐洲回來,參加康德「即位」大典,旋奉命繼多田駿少將後,任軍政部最高顧問,仍兼關東軍部附。 拒見板垣成公案 板垣乘輪東返,取道上海,電召滿洲評論社主幹小山貞知,同往南京訪問,經駐華武官聯絡,謁中山陵獻花,訪政府軍政當局,且請謁先生致敬。據說當時板垣實由軍部授意,相機與蔣先生談論「滿洲問題」,「打診」(探詢意)進一步解決「滿洲問題」的可能性。 但板垣在南京住1星期,始終不得要領,悵然而返。塘沽協定是休戰,非和平,為取得和平,當然有續談政治問題的必要,這是應有的認識,假使板垣在南京,見著國府最高當局,打開直接談判之門,民國23年3月的「滿洲帝國」,可能展緩出現,或竟胎死腹中,亦未可知,蔣先生拒絕見板垣,不能不算失策。 次年(民國24年)3月,土肥原賢二「公開」訪華,由華北而華中,所至招待周到,在上海時,土肥原曾浼蔣先生的心腹吳忠信氏,向蔣通誠悃,亦欲繼塘沽休戰協定,獲得較永久性的協商,吳忠信一再與在贛「剿匪」的蔣委員長電商,回京接見土肥原,或由吳伴往南昌,最後蔣先生覆電「軍務倥傯,不克分身」。囑與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洽談,土肥原固極為掃興,吳理卿(忠信字)亦以蔣拒人過甚為憾。 可是「汪先生」卻不放過這一機會,除派唐有壬、李擇一到滬歡迎,並令路局備花車供訪客乘坐,抵京後作為汪院長的嘉賓,下榻迎賓館汪邸,為安全計,所有土肥原的訪客,均在汪邸延見,應酬兩日,始盡歡返滬。「汪先生」為抵制不利的宣傳起見,先由主管新聞人員,製造「土肥原在平津遇刺,捕獲嫌疑犯一人」消息,送各報登載,以示此次招待,為免外交生出枝節,並非隆重延賓。然而「汪先生」和日本人,發生好感,實已由此時開始。 板垣回「滿」,任軍政部最高顧問三數月,8月異動,繼岡村寧次之後,轉關東軍參謀副長,西尾壽造任參謀長,一切均付板垣主持,民國25年3月晉級中將,升任參謀長。26年3月,始轉任廣島第5師團長離「滿」,以憲兵司令副參謀長東條英機繼任。 因塘沽協定的關係,關東軍已取得華北政權──北平政整會,軍分會交涉對手的合法地位。在此時期,所有對華北的一切措施,均由關東軍主持決定,天津駐屯軍,系統雖仍舊貫,事實上與關東軍已有主從的關係,板垣南京舊事,耿耿於懷,他已意識到國府最高責任者,對日交涉,至少有意規避,中日關係一時難望好轉。 因此少壯將校積極的,強硬的主張,又趨於抬頭,24年的何梅協定、國軍撤退、黨部撤退、香河事件、通州事件,道一連串的不祥事件,先後演出,華北政整會無疾而終,華北5省自治運動,甚囂塵上,結果殷汝耕的冀東22縣防共自治政府自行建立於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宋哲元政權半獨立性的革命成立於後,華北的半壁江山,在七七事變以前,事實上早已風雲變色,非我有矣。 這在關東軍的記錄,均係南次郎司令官,西尾參謀長任內的大事,這時軍的魂靈,主持大計的,即為參謀副長,「中國通」板垣征四郎少將。板垣重到「滿洲」,作關東軍的掌舵人,由歐返國時,業已內定,板垣為中日關係,為個人功名,也確有「碎骨粉身」,從頭做起的「覺悟」。 設特務加緊侵華 老一輩日本軍人的「中國通」,沒有中國,他們的功名,便也無所寄託,他們謀中國之心,不必有愛於中國,然而他們的主張和作風,究竟還不似徹頭徹尾的「侵略者」,板垣、土肥原,以及岡村寧次都是一樣。 板垣征四郎不久便被任近衛內閣改組後陸軍大臣,板垣由中將師團長,且係台兒莊戰役失利的前線指揮官,居然榮膺大命,驟儕台閣,為日本軍部的「當家人」。他所挾以自重的,仍憑藉「滿洲」的淵源,對華的知識,積極的收拾「中國事變」,遂行近衛「內閣使命」,以副日本全國的要望。 板垣抵任以後,即著手考慮對華政策的新出發點,由大本營設置特務部,遴選一流的「中國通」任部長,派赴中國,擔任艱鉅的現地工作。當時特務部長人選,由土肥原賢二、磯谷廉介兩中將,加以周到的銓衡。 土肥原、磯谷均係陸士16期「秀才」,與板垣陸相同期,土肥原任地多在華北與東北,磯谷則在華中與西南。結果土肥原因與「滿洲」、華化關係較深,決定大本營特務部長,磯谷廉介轉任關東軍參謀長。(待續)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