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水:我的兩次「政治犯」勞教經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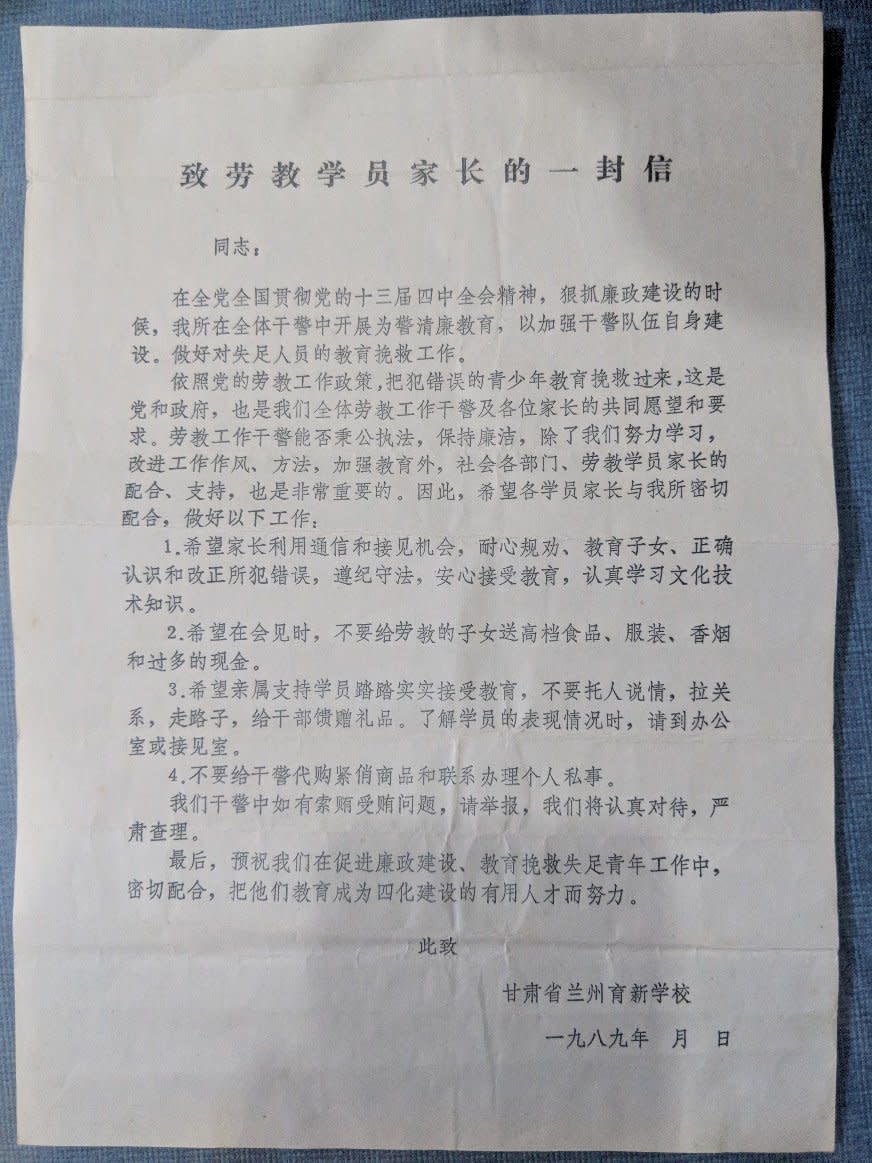
剛才帶我倆進來的獄警在辦公室喊叫「叫新來的學員進來!」。囚犯催促「安子」在叫,快去中隊辦公室。我這才看清,這位獄警非常年輕,短髮,身形瘦削,皮膚煞白。他面無表情地自我介紹是九中隊指導員。他邊翻閱我倆的檔案,邊宣佈獄規所紀「五要十不准」。隨後,我們填寫了入獄登記表。他最後厲聲命令道,你們不要傳播蘭州和北京發生的反革命動亂,小心我關你們禁閉。
我辯解道,我們不是罪犯,是愛國者,參加組織的是愛國民主運動。指導員站起來狠狠地說,你們還愛國?誰說你們是罪犯啊?愛國會燒死那麼多戒嚴軍人?!田達海回答,不是學生幹的,他們開槍殺人。他又警告說,中隊現在沒空房,否則單獨關押你們,讓你們好好反思反思。
後來,我才漸漸知悉,囚犯私下起外號「安子」的指導員,名叫安天福,他為什麼怒火沖天。原來他是獄警世家,其父就是本所獄警,其妻是獄部醫生。他曾在新疆邊防部隊服役,退伍後子承父業。再後來,一位「三進宮」囚犯告訴我,安子當兵前可是平安台一帶的「小惡霸」。
我分在一分隊,田達海分去前院的二分隊。我與田達海揮手告別。他拿著行李被帶去前院二分隊。
圍攏而來的不少囚犯,裸露的肉體上刺滿紋身,脖頸、前後背、手臂和手背,獨露臉部。在看守所一個月,見識過殺人犯等各種危重刑事犯,我心裡反倒很坦然。
我主動告訴兇神惡煞的圍觀囚犯,一個月前在北京長安街抵抗過槍林彈雨,他們馬上肅然起敬。此後,入獄「新兵」常見的「見面禮」免去了。囚犯們低聲打聽:「你是大學生?哪個大學的?」「聽說北京開槍了,死人了沒?」「抓了多少學生?」「啥時候放我們?」……在看守所習慣了老犯的閉塞和好奇,我樂於告訴他們北京屠城真相。
有人拿來一個小馬紮(折疊椅),有人拿來髒汙的圍巾,有人端來一盆水,有人搬走所有行李。在看守所很少能曬到陽光,加上饑餓,我的身體浮腫、虛弱;那時理的光頭,頭髮已漸長。他們將剃鬚刀後面的刀架卸掉,用一根火柴梗墊支,然後旋緊螺絲。刀刃可最大角度地貼近頭皮。如此,給我刮的光頭,摸不到發根,肉乎乎的,還刮破幾處頭皮。
我們曾在看守所非常抗拒理光頭,這有關個人尊嚴;沒有一款法律條文規定,囚犯必須理光頭。同時,為抗議克扣囚糧,我們各個監倉,串通合唱《國際歌》。
看守所生活環境實在太惡劣,不能洗澡、不常洗衣,身上生滿蝨子。後來,為個人衛生計,我主動理光頭。在我以後兩次牢獄生涯中,囚犯理光頭,幾是「慣例」。唯獨在深圳收教所,反而禁止囚犯理光頭,我常犯規理光頭。對著幹,其實就為表明一種無聲的抗爭。自從深圳出獄後,我理光頭十多個年頭了。
我被安置在緊挨管教值班室的一組。一個監倉為一個小組,滿編21人。分隊大院,一溜五間監房,最西頭靠近旱廁那間,是囚犯個人物品保管房,專人專管。教室大小的監倉,塞滿高低鐵床,白色牆壁烏黑烏黑;辨不清顏色的地板,閃著亮光。我的床位在靠門的上鋪,伸手就到窗外。有人替我鋪好了床鋪。靠近裡側牆壁,單獨靠放一張單層鐵床,前面放張掉漆的桌子。桌面垂懸而下的白布上,畫繪一隻一米見長的回頭上山虎,張著血盆大口,竟也惟妙惟肖。
組長叫劉國強,跟我同齡,穿一身嶄新的草綠色軍便服,戴綠色軍帽。勞教所沒有配發統一囚服,囚犯大多自備草綠或深藍色軍警服,戴草綠軍帽。當然不能佩戴帽徽和領章。他的馬仔看起來不到20歲,狐假虎威,呵呼我馬上寫一份犯罪經過交代書。他遞上來幾張信紙和一支筆。我未搭理。組長揮手制止了小馬仔。
我問,誰有香煙?看守所禁止吸煙,我被迫戒煙一個月。緊挨我床鋪的小圓臉,笑嘻嘻地遞過來一張用報紙裁製的捲煙紙,又從被褥下翻出一袋細碎煙葉,說:「莫合煙,你抽得慣麼?」劉組長沒言聲,拋給我一支「蘭州牌」香煙。我下鋪被喚作「西固」的男子,站起來用火柴給我點燃。謝過他們。我大吸幾口,頭暈目眩,想要嘔吐。很久沒吸煙了,大口吸反而倒胃口。他們哈哈大笑起來。氣氛頓時變得輕鬆起來。
從看守所到勞教所,無異於從地獄到「天堂」。
監倉裡竟然有幾把吉它。我進倉時,有人高高坐在床頭,在撫琴彈唱。監倉門晝夜都不上鎖,可自由出入。只在夜間出倉如廁時,轉頭對著中隊院門的囚犯值班室,大喊一句:「報告,上廁所!」即可,都會被許可。
更讓我非常意外的是,監倉裡居然有三個現役軍人,分別是來自甘南的騎兵、張掖的坦克兵和榆中的通信兵。依照勞教條例規定,學員可保留公職和軍籍,也即他們服滿勞教期,可以回原單位、原部隊繼續工作、服役。只是他們的帽徽和領章被撕掉了,個人被服鞋帽全是軍隊用品。唯獨參加學運的我們被從重處罰,開除學籍,這是後話。
我在勞教所的自由空間大大得到延展,能經見陽光白雲、風雪雨露和春夏秋冬,能讀書、寫字,能從視窗望見院外嘩啦啦作響的楊樹綠葉。看守所擁擠的水泥炕通鋪,變成勞教所的單獨床位。我打定心思坐滿一年三個月牢獄,455天。我在床邊牆壁上用手指甲刻下一道杠。
在看守所時,蘭州大學、西北師院、甘肅農學院、蘭州商學院、西北民院、甘工大、蘭州醫學院、甘肅中醫學院、蘭州鐵道學院,還有甘肅省物資學校、甘肅省財政學校等幾所中等專業學校,以及蘭州幾所中學學生,共計幾十名「反革命學運分子」,串通達成共識:服管不認罪。這也是我在勞教所的底線。
甘肅省勞教所實為一座勞教農場,前身是蘭州八家單位的「右派」勞教農場。囚犯們種植小麥、玉米和大豆,養豬牧羊;一大隊女犯打理蘋果園。我不怕苦役。文革十年,我隨「老幹部」父母下放貧瘠的西北農村,住窯洞、點煤油燈、深溝挑水、學校組織支農、砍柴、挖藥材……所有的苦厄日子我都有歷練,所有的農活我都幹過。
籃球場邊高大的監牆上,用黑色塗料刷寫著一人高的六字勞教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教育挽救第一,生產勞動第二。我倒覺得,恰恰相反或徒然。共產極權最大的罪惡,即妄想用最殘酷、最原始、最繁重的肉體勞動和長久的饑餓,讓你為一杯水、半個饅頭主動屈從。所謂勞動改造,就是通過對肉體的折磨,從而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主動放棄異端思想和異議行動。專制政權往往盲目自大:對於絕大多數人,肉體可以主宰精神;可它常常低估:有的人,精神可以主宰肉體。
1918年蘇維埃靠暴力奪取政權後,列寧提出鎮壓反革命、用勞動改造靈魂的邪惡國策,由此誕生遍佈蘇聯蠻荒大地上的勞改、勞教「古拉格」集中營。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全盤複製,中共更不例外。
我們趕上了農忙季節。
劉水 中國資深媒體人,曾任香港大公報·大週刊深圳總編部採訪主任、《南方都市報》駐深圳記者兼編輯、《深圳晚報》記者。現為自由作家,政治異議人士。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