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食懷念姆媽進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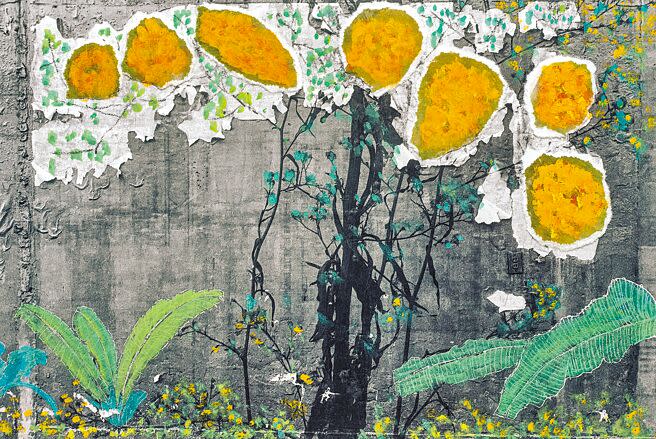
夏天是竹筍的季節,在傳統市場買了大文山區產的綠竹筍,轉屋洗手做羹湯。
綠竹筍去殼,切片。從冰庫取出四分之一隻雞,剁小塊,薑切片,蔥打結,加兩塊豬腳添香,泡幾顆段木鈕釦香菇,鋪上大白菜,用砂鍋燉將起來。
煮食是懷念姆媽的一種方式,心裡想著佢做菜的味道,試著做將出來。餐館吃不到冬瓜封,自己動手做。高麗菜封,豇豆乾排骨湯,高麗菜乾雞湯,一一做將起來。
姆媽手腳麻利,是左手慣用者,卻可以左右開弓,除了食飯用右手拿筷子,大部分家事、農事均可左右手互換。譬如切菜頭曬菜脯,拿個小板凳坐在腳盆邊,砧板橫跨腳盆,左手握菜頭,右手刷刷刷切將起來;右手切累了換左手,變成右手握菜頭,左手揮刀如飛。有一回同學來家裡,姆媽到雞塒抓隻雞,去竹叢鏟麻竹筍,約不到一小時,筍子雞已經上桌。當然殺雞時我得幫忙抓著,以及負責拔毛。
老屋禾埕前有一個菜園子,入口處種了兩棵七櫞茶,煮客家茄子時,加大把的七櫞茶。芹菜、韭菜、湯匙白(青江菜)、高麗菜、明豆(四季豆)、長豆(豇豆)、菜瓜、瓠仔、刺瓜、黃瓠(南瓜)、冬瓜,四季迭替,菜蔬隨時鮮。小小的菜園子供應了一家蔬食,除了豬肉,鮮少買菜。
母親是煮食高手,動作快,火候準,常被辦桌師傅拉去當副手。每天早晨父親五點出門下田,母親四點半起床,起大灶燒飯、煮食。客家人早餐不吃稀飯,母親煮兩三道菜,半小時了事。我想母親可能遺傳了外婆的好手藝,外婆八十歲了還去粄店幫忙做粄,當然不是因為缺錢,粄店老闆無非給外婆幾個小錢當零花。小舅當過潤泰紡織中壢廠廠長,大概不會養不活外婆,而且還有大舅,外婆祇是找個活兒做做,好度閒日。
客家吃食簡單不繁複,炒青菜就炒青菜,極少配東配西,偶爾加個五花肉片或肉絲炒,沒太多花頭。譬如煮黃瓠湯,切塊,連籽一起煮,加薑片和赤砂糖,簡單明快。後來我看城裡人做西式南瓜濃湯,將南瓜蒸熟,壓泥,炒馬鈴薯或洋蔥,加牛奶燉煮老半天,工序繁複得要命。我自己寧可做客家黃瓠湯,簡單又好食。印象裡姆媽做客家小炒似乎不加豆干,五花肉、魷魚加芹菜,就炒將起來,加豆干和蔥段的客家小炒,是後來在餐館吃的。
知天命之年,友人問我下一個興趣會是什麼?我開頑笑曰,搞不好是做菜,不意一語成讖。起心動念煮食,說起來有點兒竹篙兜菜刀。某年友人送了我一條臘肉,在冰箱裡放了幾天,想想不是辦法,總得煮來祭五臟廟,於是腦子裡浮現蒜苗臘肉。某日下課轉屋路上,買了幾顆蒜苗,一顆高麗菜,開啟我的煮食之旅。因著友人送我一條臘肉,從此我成為自煮團成員,簡直是種瓠仔生菜瓜。
或許是遺傳了姆媽的煮食基因,洗手做羹湯對我不算太難。其間當然有許多幫忙指導的朋友,此處不一一縷述。其中乾妹陳淑蘭是煮食百科全書,本省菜,外省菜,中西餐,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平日煮食我會做一道姆媽菜,練一道館子菜(俗稱功夫菜),兩路並進。姆媽的菜式比較簡單,館子菜須費工夫。如果是新菜,我一般會練三次,第一次照書做,第二次以己意稍加調整,第三次從心上化為在手上。譬如做雞丁,我買五支雞腿,把辣子雞丁、蔥爆雞丁、宮保雞丁、左宗棠雞、麻油雞,依序做一遍。但總不能每天吃雞,所以我是每三天練一次。反覆三次,花了一個半月才練完。可能我比較笨,學啥都要比別人多費工夫,才能從心上化為在手上。煮食如此,練字亦然,我一般臨帖差不多要到六、七十通方能背臨,做菜則要三、五次才得心手合一。
姆媽過身廿九年了,想起退伍後姆媽因退化性關節炎,無法剁雞,於是由我代勞,乃得近身觀察姆媽煮食。
姆媽過身那年我卅四歲,一九九三年六月取得博士學位,十二月三十日姆媽大去,佢的身影永遠住居在我心底。
姆媽高大,壯碩,漂亮,是我內心深處永遠的女神。如果我對壯碩的女生特別感到親切,我想,那一定是因為姆媽的緣故。
一九八九年春天,陽光溫柔地灑在屋後的溪流上,我正忙著準備博士班入學考試,三姊從故鄉花蓮打電話來,告訴我姆媽病重的消息;我匆忙收拾簡單的衣物,到松山機場接姆媽與三姊,一路飛馳到林口長庚醫院。經過繁瑣的檢查手續,醫生通知我們唯一的辦法是動截肢手術。
手術在台北國泰醫院進行,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那一天也是我遞辭呈的日子;在病房我一邊忙著照顧姆媽,一邊倚著病人進食用的餐車寫研究計畫,晚上則藉醫院微弱的燈光看書,準備考試。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只記得姆媽的手術很成功,康復後回花蓮休養;我則通過考試,再度到指南山下做一名歷史學徒。我總是想起那些年的悲苦歲月,姆媽病歪歪地躺在床上,三姊辭掉工作全心照顧,還未完成學業的我一邊在報社打工,一邊研讀博士課程。
一千多個日子過去了,姆媽依舊祇能坐在籐椅上發獃,一切的生活瑣事都需要人照顧;我忙忙碌碌地上班,上學,修課,考試,寫報告,寫論文;一切的一切,彷彿還是昨天。然而,就在論文通過學位考試的那年冬天,姆媽撒手人寰,遠離伴隨佢十數年的病痛,留下未曾盡過孝道的我。
來不及告別,我內心深處有著無以撫平的傷痛。
如果親情是生命的倚靠,父母與我之間的情分竟薄如桑紙;一九八一年大學畢業那年秋天,賦別三月,父子已人天永隔;而獲得博士學位那年,姆媽又等不及我邁向新的生命旅程,即匆匆告別人世,為人子的我亦唯把缺憾還諸天地。我想很少有人如我之遭逢,父子緣淺,母子相隔,縱是千萬呼喚亦尋不回家的溫暖。雖然父母遺傳給我樂天知命的性格,讓我在死命的樂觀主義支撐下走過人生種種苦難,並且學會用微笑面對一切的困難。而每當午夜夢迴想起這些,時覺人生多苦,憂患實多。而我仍昂首闊步,迎向生命的每一場遭逢,就像當年父親和姆媽,背著襁褓中的二姊,走過長長的臨海路到後山拓荒。
父親是臺灣東部拓荒的第三波移民,在戰後的艱困年代,湖口山上的茶樹因戰爭期的荒廢,已無法養家活口,父親在大伯的慫恿下到花蓮拓荒。在前兩波移民闢剩的僅存少許荒埔地,挖樹根,闢草萊,尋覓些許可耕之地,插幾畦番藷,養豬餵雞,以及耕種鯉魚尾的那片田。姆媽是窮苦人家出身,跟著父親除草挖地,默默吃苦。直到許多年後我隻身回到假婆(客家人稱外婆為假婆)家,假婆猶自淚眼婆娑訴說當年阿桃妹到後山討生活的陳年舊事。假婆說阿桃妹到後山以後,佢整整哭了一個月,耽心掛意後山的生番不知還吃不吃人。尤其彼時大舅被拉去做軍伕,滯留南洋,生死未卜,大妹仔(大妹仔:客語稱女兒為妹仔,大妹仔即大女兒之意)阿桃妹又到後山去,假婆日日心肝像針蕊,刺著隱隱作痛。當我第一次隻身出現在假婆面前,假婆真是高興極了,逢隔壁鄰舍就說我是阿桃妹的大賴仔(大賴仔:客語稱兒子為賴仔,大賴仔即大兒子之意),從花蓮來看佢。彼時猶未熟悉臺灣東部拓荒史的我,並不是很能體會假婆的心情,直到許多年後我為洄瀾文教基金會撰寫歷史通俗讀本《歷史花蓮》,始知當日到後山拓荒的艱苦。
一九四六年春天,父親帶著姆媽,背著襁褓中的二姊來到花蓮豐田。將賣掉湖口山上茶園所得,在鯉魚尾買了八分瀾仔地,從此定居豐田,一個地圖上不太找得到名字的小山村。十年後我和三姊方始先後出世,拓荒年代的艱苦歲月殆可想見。
姆媽天性開朗樂觀,我從不曾在佢臉上看過愁苦,縱使物質生活如此窮困,佢仍是每天開心地和父親一起下田耕種,屋前的菜畦永遠有採摘不完的各式蔬果。春秋二季蒔田時節,姆媽會參加父親和村人合組的蒔田班,負責鐐秧仔,挑秧苗,像蒔田班的大阿姊。父親木訥少言,姆媽則風趣幽默,永遠帶著燦燦然的笑容。我一直喜歡看姆媽戴著斗笠,斗笠上包一條彩色大頭帕的模樣,甚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天下的姆媽都應該是那個樣子。姆媽因為手腳俐落,在蒔田班博得班友的好評,每次組蒔田班時,第一個想到的挑秧娘就是佢。尤其因為姆媽不僅是左撇子,而且工作時可以左右開弓,右手鐐秧仔鐐酸了換左手,右肩膀挑累了換左肩;舉凡一切使刀挑擔之類的工作,姆媽都可以一人當兩人用。我第一次發現姆媽有這個本事是在曬菜脯時,姆媽在大腳盆上置一塊砧板,右手握菜頭,左手拿菜刀,悉悉刷刷地切將起來;過了一段時間,換成左手握菜頭,右手拿菜刀,繼續切將下去;坐在門前墀階上的我,簡直看得目瞪口呆。後來我才發現砍蔗尾,剁蔗栽,撒肥,鐐秧苗,姆媽都有本事左右開弓,難怪可以一人當兩人用。
身為客家餔娘人(客語稱婦人為餔娘人),姆媽是標準典型,家事一手包,還要跟上跟下隨父親耕種,我很少看到像姆媽身手這麼俐落的婦人,農事做得幾乎比男人還好,家事更是一把好手。做飯燒菜當然是基本功夫,難得的是姆媽做粄深得假婆真傳,菜包、紅粄、蟻粄(蟻粄:客語稱艾草糕為蟻粄,蓋艾草揉碎後的斑點像螞蟻故名)、粄粽,無一不佳;尤其姆媽做的菜包,用柚葉襯底,那種獨特的香味,令我數十年後猶自口頰留香。姆媽包粄粽用月桃葉,葉香襯得粄粽色香味俱全。許多年以後,我在外地只能買到麻竹葉包的粄粽,雖然那已是難得的客家吃食。
我想如果不是鄉下人家的醫學常識不足,姆媽亦不會因退化性關節炎而不良於行二十年,對現代醫學而言,這並不是太嚴重的病,甚至換個墊片或人工關節亦不是什麼不得了的大事;但姆媽初病之時,三姊和我識世未深,二十歲的年紀,什麼事都懵懂,姆媽就此一路耽誤,等我略識人世,姆媽兩腳已糾屈難行,各種慢性病纏身,從糖尿病到高血壓,無一倖免;從退化性關節炎到心肺衰竭,舉凡老人家身上可能出現的所有慢性病齊集,三姊與我亦惟徒喚奈何。雖然不曾費心統計,但我想姆媽進出醫院總不下兩百次,如此漫長的歲月,我和三姊不曾向任何人訴苦,因為訴苦也沒有什麼用,要面對的仍須面對,我尤不願露出悲苦的容顏,因為姆媽生病以前從不曾對命運遭逢有何怨言,我知道佢老人家一定不願意看到我為此愁苦。
許多年又許多年過去了,母親截肢後的日子只能坐在輪椅上發呆,我每次返家亦唯暫時做做三姊的替手,為姆媽洗身換尿布;研究所課業和晚上的打工耗費太多精神,使我連抱怨的力氣都沒有,尤不想向命運低頭。我總是用父親和姆媽到花蓮拓荒的精神鼓舞自己,如果那樣艱困的歲月都可以度過,眼前的遭逢又有什麼度不過的呢?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為自己打氣,相信長夜漫漫終將黎明。
然而,當黎明來臨的時候,姆媽已經看不到了。在我完成學位返回母校任教那年冬天,姆媽撒手人寰,連差一天的新年都沒能趕得及。我常常想,如果不是父親意外過身,如果不是我執意要走學術之路,一切的一切是不是會有所改變?在生命轉彎的地方,我並沒有太多選擇,姆媽也是。如果那一年佢不隨父親到後山拓荒,如果那一年退伍後我沒有離鄉負笈異地,如果那一年佢沒有不良於行,是不是生命可以有另一種選擇?而生命的程途繼續往前,我並沒有太多停佇思考的機會,只是一路行去,直到姆媽離開這世界,離開佢那未曾盡過孝道的兒子。
於是我用煮食和姆媽和解,彌補來不及告別的遺憾。每當我拿起菜刀的時候,姆媽高大壯碩,臉如滿月,臉上永遠帶著笑容的身影,彷彿就在身邊陪伴著我。(本文摘自《秋光侘寂》一書,允晨文化提供)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