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珊珊》垃圾處理是集體的思維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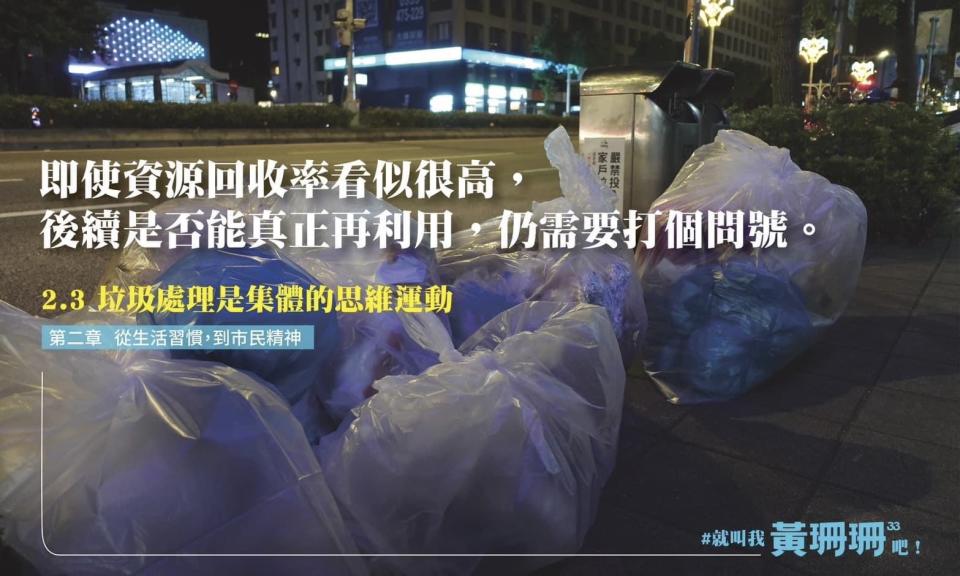
【愛傳媒黃珊珊專欄】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垃圾。
這句話,在現代工商業發達的社會,幾乎是變本加厲了。歷史上記載過的公共衛生政策中,通常在越大的城市,人口越密集的區域,垃圾的問題越容易留下記載。如同《韓非子》曾經記載,殷代的律法禁止將垃圾丟棄在道路上,違者處斷手之刑;或是公元前五 百年的雅典,法律規定垃圾必須傾倒在距離城市一英里的地方,維持市容且避免疾病。
在古羅馬的龐貝古城,資源分類回收已是市民處理垃圾過程中的優先步驟,當時候他們 與垃圾的距離,看待垃圾的眼光,可能還比今天的許多市來得更先進。他們並沒有在遠離城市的地方掩埋傾倒垃圾,而是將垃圾處理的場地選在市郊最繁忙的地帶,並在這個區域進行分類和回收的步驟。
於是垃圾離開一般家庭以後,並不像現代的我們倒完垃圾以後,就鮮少關心它們的後續 處置,而是在龐貝城市民的必經要道回收再處理。考古學家發現這座被火山噴發掩埋的 大城市,一些傾倒的樑柱內部顯露出的破瓦罐,是他們廢物再利用成為建材的見證。
龐貝城與垃圾的距離,不代表龐貝人並不重視城市的公共衛生品質,而是在城市建立之初,就圍繞著不同的價值排序,來形成他們的生活方式。
龐貝城的垃圾處理場將回收看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並沒有遠離日常生活現場。就像學者也發現,龐貝人會將先人的墓園蓋在相同的地段──公墓、垃圾處理場,這在台灣, 往往是受到鄰避效應、遠離住商密集的地帶,龐貝城卻將死亡與垃圾分類處理放置在交 通要道。這兩件事顯示了龐貝古城的建城,人的生活,是圍繞著與現代城市不同的原則 展開。
人的死亡與記憶,物的廢棄與重生,在現代化的城市隔得很遠,在龐貝城居民眼中,卻都是與生活親近而不可分割的重要過程。
只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我們精心製造生產的不同商品,連帶產生的許多包裝,還有新研發的材質,讓垃圾的回收再利用變得更不容易。商品打從生產之初,就下了一個銳利且唯一的定義,分離出無法再次利用的「廢棄物」,將垃圾從生活中涇渭分明的排除開來。今天的都市規劃,垃圾處理往往排在現代人生活中最末位的地方。
台灣至今的垃圾處理回收,固然有它值得讚許的地方。然而,如果我們像龐貝人一樣, 從價值排序的優先順序來思考,在這些政策、資源回收率的數據背後,台灣至今的垃圾處理方式,又要碰上了新的問題。
在 1990 年代興建的 26 座焚化爐,運轉至今也是時候開始面臨了老舊、效率降低的毛病。 再加上台灣的垃圾量又在逐年增加,特別碰上了疫情,店家外帶、使用環保餐具的用量大增。焚化垃圾,首先要考量的是垃圾的熱值。當初設計焚化爐的時候,家戶垃圾多以廚餘、紙類為主,其熱值較低。隨著今天熱值高的塑膠垃圾比例升高,這也意味著焚化 爐能夠處理的垃圾量就會下降。加上國際間環保意識抬頭,這座島嶼上的垃圾問題又逐 漸成為檯面上的燃眉之急。
當年的中壢垃圾大戰之所以發生,正是因為垃圾量增長,卻又沒有規定處理方式,才使得無處可去的垃圾溢滿街頭。而現在面臨焚化爐老舊,逐年增加的垃圾量已經應接不暇, 得要重回掩埋、暫存的窘境,以及資源回收碰到的瓶頸,當年各縣市拉扯的垃圾大戰眼看要捲土重來。
台灣垃圾處理碰到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垃圾量多到無法消化,縱使在垃圾量攀升的情況下,全台灣焚化爐的量能仍然有餘裕,然而分佈的區域並不平均,多集中在北、高兩地。 「不患寡,患不均也」是垃圾焚化處理這塊目前的困難。在法規上,中央缺少調度各地焚化爐的權力,可是當垃圾處理問題碰到地方本位主義的時候,往往就會眾人自掃門前 雪,各縣市之間將垃圾處理視為燙手山芋。
儘管垃圾總要有人來處理,可是沒有人願意在自己家門做這件事。
有興建焚化爐的縣市,就會碰上在地居民對於代燒垃圾的反彈;沒有興建焚化爐的縣市, 無法處理的垃圾同樣令人頭大。而更深層的危機,是我們以掩埋和焚化做為處理垃圾的最終歸宿,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改變。誰都不希望掩埋場、焚化爐設在自家門前,可是轉移至其他地方,眼不見為淨,也並非真正解決問題。空氣汙染沒有邊界,水汙染沒有 邊界,以焚化、掩埋做為我們對垃圾的最終理解和歸宿,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棄用」 的想法。
其實台灣在資源回收的落實程度是非常令人驕傲的,只是末端的處理,卻沒有真的做得很確實,使得民眾整理分類的功夫,最後卻又白費了。過去資源回收的制度,隨著回收類型越來越多,目前的大分類,其實並不能真正反映到後續處理的步驟,複合材質處理的成本也偏高。於是很多資源回收的餐具、容器等,依然是進到了一般垃圾焚化處理的 程序中。即使回收率看似很高,後續是否真正走到能再利用的用途上,仍需要打個問號。
另外在疫情期間蓬勃發展的,還有網購帶來消費模式的改變,帶來的銷售額成長十分驚 人,卻也是因為網購使得產品運輸、配送的方式越來越分散,每年增長的垃圾量也非常 嚇人。包材的耗用不再像是實體買賣,一大箱一大箱送達實體店面,而是必須越來越精 細,以每個網購買家為單位進行包裝,再送至各家取貨店點和超商。
僅僅是消費形式的改變,中途就多產出了這麼大量的廢棄物──台灣人網購,光是一年 就用掉一億個包裝,而這個數字還正在隨著疫情網購數量增加而繼續上漲。
一億個包裝,最少最少,也足夠繞地球三圈以上──然而,沒有誰能夠乘著廢棄物包裝 環遊世界。一億個包裝,也許曾經可以有更好的去處,更好的用途,而不只是在商品寄送的旅程中, 用完即拆即丟。
作者為前台北市副市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