黏人的花蓮土 讓文學開出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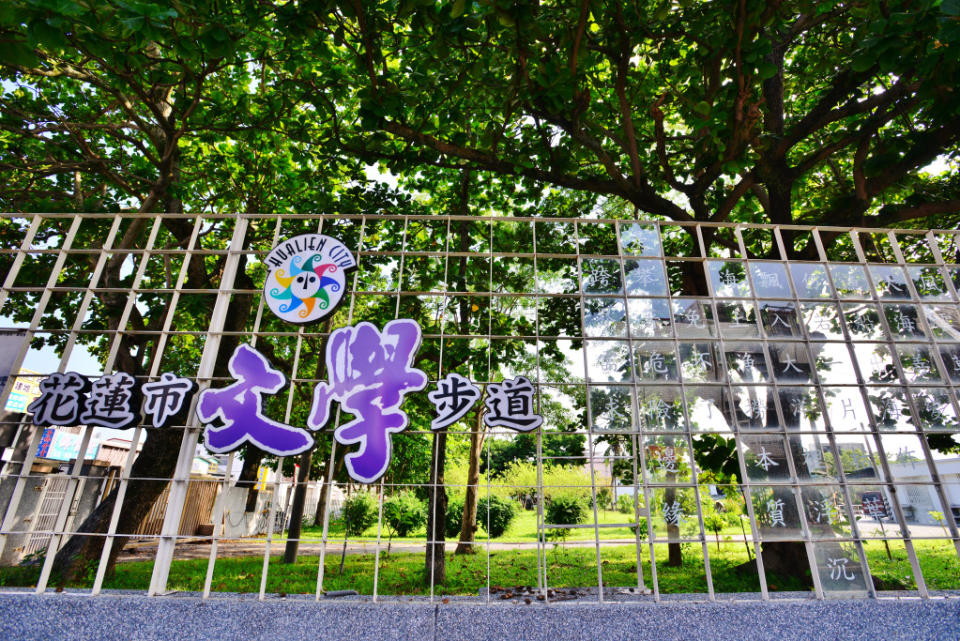
作家陳雨航獲得開卷好書獎的作品《小鎮生活指南》,是一部沒有特別指出地點,卻被普遍認為是以六十年代的花蓮為背景的小說。陳雨航在這部備受矚目與好評的小說後記中寫到,他回到花蓮東華大學駐校,望著草坪遠處學生宿舍的燈光,前塵往事波濤般湧來,「這裡原是我小說創作的原點啊!後來我去了哪裡?」 花蓮出生成長的陳雨航,對花蓮的追尋和情感的依附,可以看成是許多花蓮文學家對這塊土地情感的縮影。陳雨航在花蓮出生,是王禎和在花中教書第一年的學生。雖然後來離開花蓮到外地發展,但鄉愁似乎永遠都是鄉愁,童年的故鄉,一直都是人生的原點。 王禎和,可以說是花蓮最早被熟知的作家。花中畢業後考上臺大外文系,後來回花蓮教書。從嫁妝一牛車、兒子的大玩偶……等等等等,王禎和將花蓮的地景地貌和風俗民情融入小說中,花蓮成為小說獨特的舞臺和語言,形成獨樹一幟的格局,一直傳唱至今,成為經典。從王禎和以降,許多花蓮的作家,都與花蓮中學脫不了關係,花中窗戶望出去的白燈塔,即使已經消失,卻如星宿一般,永遠照亮著一波波拍打上岸的花蓮文學浪潮。 花蓮一直以來地處邊陲、交通不便加上地景特殊,以及多種族融合的特質,一直具有某種神秘而又格外浩瀚的氣質。或許是因為這樣大山大海而又與世隔絕的浪漫氣息,花蓮似乎盛產詩人。最有名的就是早慧而創作不輟的詩人楊牧,楊牧從高中開始創作,散文和詩兼有,他的詩作已經集結成三大冊《楊牧詩集》,一路影響臺灣詩壇的發展。楊牧創作與學理並重,因此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取得平衡,不論寫詩或散文,都是情理兼具節制,卻仍充滿濃厚詩意與啟發。 除了楊牧,如今正值壯年、出身花蓮的詩人還有陳黎、陳克華。陳黎不斷進行各種可能的嘗試或實驗,將詩詮釋得更生活化、活潑化,也讓詩顯得更平易近人,他的《動物搖籃曲》、《小丑費畢的戀歌》、《親密書》、《島嶼邊緣》等都是代表,他長居花蓮,但他讓詩與生活以及中央山脈的阻隔做了微妙的平衡。雖然住在後山,他不間斷同步更新文學脈動,持續翻譯各國詩作,包括聶魯達、辛波斯卡的詩集以及日本的俳句等等,持續為現代詩注入許多不同的能量和火花。 也是醫師的詩人陳克華,曾是知名作詞人,詩集《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即讓他聲名大噪,歌詞〈臺北的天空〉就是他年輕即富盛名的作品。陳克華擅長詩意語言意境的營造,尤其是情感和語言唯美和浪漫的拿捏相當到位,但他並不滿意,也從不侷限自己,最有名的即是推出《欠砍頭詩》,後來更以同志身份出櫃,推出情色詩,另外他也對佛經有深入研究,常將佛理入詩,也畫油畫開畫展,以自身實踐不同層次的人生面貌,活出真實的自我。 從前人開拓撒種,花蓮的詩路一路走來,年輕的詩人或許是吸收了充足的養分,產能質量不但不見遜色而是更加全能,常常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或小說,並且不放棄嘗試或探索其他可能性。包括花蓮中學畢業的吳岱穎和林育德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吳岱穎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新詩首獎、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國軍文藝金像獎小說首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首獎,及花蓮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等,獎多不及備載,而更年輕的林育德,除了寫詩,小說成就也很可觀,他的〈阿嬤的綠寶石〉獲得第十八屆台北文學講小說組首獎,最近更出版摔角小說《擂台旁邊》。 除了詩,花蓮散文作家最可一提的就是陳列。經歷政治囹圄的陳列,也曾投身民主從政,但他身上的文人氣息從未改變,甚至後來歸園田居,都是一派清淡恬然。陳列的散文和他的人一樣,平淡溫和卻耐人尋味,看似簡單卻餘韻無窮。《地上歲月》、《永遠的山》都是1990年代出版,都曾獲得大獎,是值得令人一讀再讀的作品,而獲得2013年開卷十大好書、2014國際書展大獎、聯合報文學大獎以及臺灣文學獎的《躊躇之歌》,是他在政治與文學之間的拉扯以及他沈澱之後的信念與反思,以及更大的連結。 小說,從王禎和開始、陳雨航乃至林宜澐乃至吳明益,小說家在花蓮,創造不同的故事。林宜澐早期推出《夏日鋼琴》、《耳朵游泳》等雋詠清新而帶有實驗性質的小說,也會有《東海岸減肥報告書》這種幽默自嘲卻洞見花蓮風土的散文,林宜澐風趣幽默,但小說卻顯露其嚴謹以及觀照社會的小說家眼界,擅長在幽默逗趣之中,反映現實的荒謬。最新作品《海嘯》,仍是以故鄉為背景,探討著人性和暴力。 嚴格說來,深受年輕一代歡迎的吳明益不算花蓮人,他應該也不喜歡自己被歸類,但長期在東華大學教書,吳明益與花蓮已經產生深遠的連結。吳明益涉獵很廣,他年輕開始攝影,觀察社會,前兩年推出結合攝影集與札記結合的作品《浮光》;他長期研究臺灣自然生態書寫,出版三大冊相關論文,他的《迷蝶誌》、《蝶道》有著自然與感性以及人文結合的寬闊和厚度。他對蝴蝶的研究以及對大自然的親近,乃至於帶著學生到出海口觀察水鳥生態、著手繪畫記錄等等,吳明益常以一個身為觀察者不介入自然但情感卻在其中的謙卑態度,反而讓他的作品內涵和感動獲得讀者共鳴。 吳明益對自然的觀照也反映在他的小說上,他深受歡迎具有魔幻色彩的小說《複眼人》,加入了海水上升、太平洋垃圾渦流、原住民和少數民族傳說等元素。後來他的《單車失竊記》,他深入研究老單車,甚至騎著老爺單車參加各獨立書店的新書發表,雖然身處在學院之內,但吳明益許多真誠而開放的想法獲得年輕一代讀者的認同。 方梓,則是花蓮一直持續創作的女作家代表。方梓創作文類以散文為主,她可以寫《采采卷耳》《野有蔓草》講蔬菜和生活,也可以寫以女性移民為主角的小說《來去花蓮港》,扒梳歷史、土地、族群和女性意識以及不同語言的呈現,也獲得吳濁流文學獎的肯定。 此外值得一提的花蓮作家,還有廖鴻基。高中畢業後未升學而開始出海捕魚,漁民廖鴻基堅持走另外一條路,後來研究鯨豚生態、乃至創立黑潮文教基金會,「討海人」廖鴻基用親身的經驗編織成像漁網一樣堅實的文字,有海味與人味,粗糙有鹹味,是另一種充滿力量的生命,他甚至開創所謂的「海洋文學」,不但讓島國的人民更深入了解海洋,也讓鯨豚、海洋議題和生態更加被重視。 而花蓮的海岸邊,也曾經住著一位知名作家孟東籬。孟東籬雖不是花蓮人,卻與花蓮關係匪淺。他年輕時曾在花蓮師範學院教書,後來到花蓮鹽寮隱居十幾年,過著清儉刻苦或說為「修行」的生活,創作了《濱海茅屋札記》、《野地百合》、《生態環境的第二十九天》……等鹽寮生活相關作品,以及許多當時生活體悟,論及自然、佛學與道家思想的著作。蔣勳曾說,他是唯一一個台灣在生活裡完成自己的哲學家。 除此之外,擔任小學教師的葉日松,以客語創作詩集;以及吳鳴,從叛逆少年到成為教授,曾獲時報散文首獎,出版《歷史花蓮》,對花蓮歷史深入研究及貢獻。還有在媒體服務的王尚智,也有許多勵志散文集深受歡迎,都是花蓮出身的作家。而曾出版《西貢小子》、《小頭目優瑪》《阿國在蘇花公路上騎單車》張友漁,在童書領域上獲獎無數,她也是出身花蓮的作家,《悶蛋小鎮》就是她以自己的故鄉玉里為背景創作的少年小說。 不論是在花蓮被灌溉成長的文學之樹,或是帶著理想移住花蓮的新花蓮人,乃至於曾是這裡的過客、旅人,花蓮這個山海小城,或許因為依傍著山海,以及山海的隔絕,族群包容混居,於是一直用自己的節奏運轉,而生成一個獨特的小宇宙,就如花蓮作家林宜澐曾說,「花蓮就是我的風土」,多重編織造就了像花蓮這樣一個小市鎮的巨大。而知名作家郝譽翔也曾在東華大學任教多年、在花蓮生活多年,花蓮印象被記憶在她的作品裡,儘管她現在已經離開東部,但她也說道:似乎沒有人認為她是花蓮人,但花蓮卻真真實實地在她的生命底層。 或許這就是屬於花蓮文學家、作家如何被歸納的範疇。花蓮,常被說成土地會黏人,其實許多創作者的靈魂和情感也一直被黏在這裡——花蓮的影子或記憶或經驗,往往成為許多作家情感的依傍之處,他們的作品裡,總會有一個獨特的形象,不論是明說或是暗喻,甚至只是一個精神,不見其形,卻貫穿其中。不論他們的身世來自何處,我們可以知道那些是屬於花蓮的。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6年/第14期(九月號) 訂閱專線:(02)23568998 傳 真:(02)23568919 Email:twmingbo@gmail.com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