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 與阿笠談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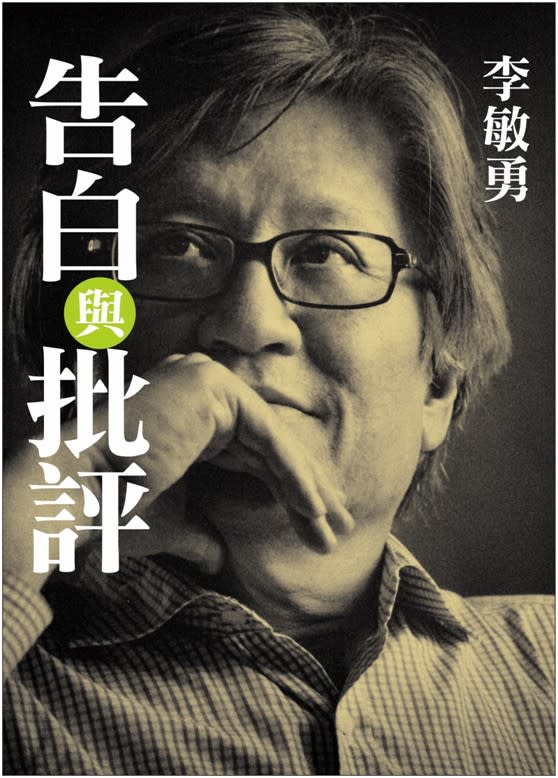
寫下這個標題,1970年代謝里法的《與阿笠談美術》浮現眼前。那是與《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齊名的謝著另一本書。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許多臺灣的文藝青年愛不釋手的書。經過四十多年,謝里法的文筆跨越到小說,一樣好看。 謝里法是對臺灣美術史著力甚深的畫家,彩筆加上文筆,讓他不只跨越繪畫與評論,簡直跨越美術與文學。每次看到他,戴著帽子匆匆走過眼前的形影,有時就近能打招呼,有時只能看望他消逝。1987年夏天,我和妻子麗明、詩人鄭烱明、音樂家簡上仁的美國之行,在紐約時,謝里法陪我們夫婦逛街、一起吃迴轉壽司的回憶,轉眼前已過25年了。 回到主題,來談詩吧!就像謝里法談美術一樣,稱呼你「阿笠」,是因為你對《笠》懷有期望,是一個在臺灣這塊土地成長的文學青年。你喜歡詩,也寫詩──這也讓我想到自己,一個在40多年前開始在《笠》發表詩作的青年。 當年的我與現在我,讓我想像現在的你和我。我不認為我與你談詩會像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十二封信》一樣深刻細膩;也不認為會像祕魯小說家尤薩《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樣精深、博大。我只想試著與一位年輕的愛詩人,寫詩者,並與想像中年輕的自己對話。 邊緣性存在 在野詩人群以獨特臺灣性支撐詩領土 1969年,我出版第一本收錄了詩和散文的書,是我一直認為青春過敏性煩惱,也就是一般所謂強說愁的詩作和散文作品。因為年輕時代的熱情以及生活感思,以分行的形式,留下的練習曲。在那時期,我是沒有社會意識、歷史意識的。 那時,我已加入《笠》,但第一本書收錄的詩作,只有極少數幾首發表在這個詩刊,其他太多發表在《創世紀》、《南北笛》與報紙副刊。對於詩是什麼?為什麼寫詩?都只是模模糊糊的認識。但我那時嗜讀文學書、哲學與社會學書,喜歡在思考與想像的世界馳騁。書店和圖書館的詩書和文學刊物也是我獵讀的精神食糧。 還沒有加入《笠》的時候,60年代的臺灣「中國現代詩」氛圍,是我面對的詩風景。從中國的新詩運動,現代詩運動到臺灣的中國性新詩運動、現代詩運動,在反共的國策宰制下,內向化和晦澀化成為潮流,詩人們在高陷的象牙塔鍛鍊文字。 加入《笠》,首先的體認就是不完全服膺文化和政治體制的「在野詩人群」以獨特的臺灣性所支撐的詩領土。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邊緣性的存在。吳瀛濤對民俗的研究比詩更投入;陳千武、詹冰、羅浪、張彥勳在《笠》像是重新登場。陳秀喜和杜潘芳格也都是重新發聲的名字。林亨泰,因為參與紀弦在《現代詩》主持的「現代派」運動,以理論提供了貢獻,而有獨特的地位;錦連雖然也加盟「現代派」,但較遁逸,並沒有林亨泰一樣的地位;白萩在當時的詩壇也有地位,他不屬於跨越語言一代,而是早慧詩人。在《笠》的社群,林亨泰和白萩,有別於其他同世代的同仁。 瘖啞的處境 國家語文雙重困厄磨礪台灣詩人之路 我的臺灣意識來自出生成長於島嶼南方的土地根源,但文化意識的形塑卻從加入《笠》,接觸以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們為主的創辦人群開始──他們懷抱著詩的熱情,卻因為國家轉換和語文轉換而備感艱辛。通行中文以「國語」的姿態卑視著戰後才學習新語言的臺灣詩人們,他們那時候大約40歲多一些的年齡,在其他國家,特別是日本,正是站上文學舞台的一代,卻面臨瘖啞的處境。雙重的困厄磨礪著他們的詩人之路。 美術和音樂也一樣,但詩畢竟以文字表述,面對的不僅是政治困境,更是語言文字的障礙。我看到《笠》的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們比美術家、音樂家更為艱難的藝術之路。但他們也比美術家和音樂家刻劃了更多現實與社會的印痕。 加入《笠》以後,我在這樣的園地發表作品,也在這樣的園地吸收養分。許多發表於《笠》的詩與詩論,特別是譯介自其他語言的聲音,大大開啟了我的眼界,認真吸收這些養分,也虛心學習前輩詩人們的文學教養,體認到詩人與詩的形式和內容條件,對自己的認識論和教養性有莫大的啟發。 我常常自喻出版了《雲的語言》──我的第一本詩和散文合集後,我才在〈遺物〉這首作品感應到自己走上詩人之路,就是這樣的意思。從青春過敏性煩惱的表現到意識到自己是一個詩人,是我在《笠》的歷程踏出的步伐。這樣的步伐仍然是我正走著的步伐。四十多年了,在一邊跌倒一邊發現的經驗中,我尋覓著詩,探索著詩,並體認到詩之為詩是有其嚴肅、深沉意義的。 你問我《笠》的事情,問我在《笠》的經歷,也問我有關詩的種種問題,讓我回想自己走過的路,也回想在那些路途上的人、事、物。環繞著詩的層層記憶浮現在我的腦海。我在這些浮現的記憶裡,重新面對一個臺灣詩人成長的歷程,這樣的歷程也許會提供你尋覓的視野,在你走向自己詩人之路的歷程,帶給你一些鑑照的光。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Yahoo奇摩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